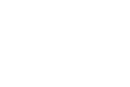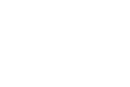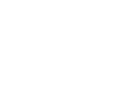来源:PG电子模拟器 发布时间:2025-12-27 17:05:01
窗外的雨下得粘稠,滴滴答答敲在玻璃上,像是谁在悄悄叩门。我蜷在沙发一角,身上裹着那条成婚纪念日他送的羊毛毯——现在闻起来只剩尘埃和一点点樟脑丸的滋味。
他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,屏幕朝下,像个熟睡的黑匣子。我知道暗码,一直都知道。成婚五年,咱们从共用一切到现在各自为营,中心那道裂缝何时裂开的,我竟说不上来。
我伸手拿起它,指尖冰凉。解锁,屏幕亮起,是他和一群狐朋狗友的谈天群。最终一条音讯是二十分钟前发的,来自一个叫“老K”的人:“明日老当地,新来的妹妹不错。”
不是一条,不是两句,是一整片扎眼的、龌龊的对话。他们讨论着那些“妹妹”的身段,同享着隐秘场所的相片,用代号暗示着价格和时刻。而他,我那个在家默不做声、连我换新发型都留意不到的老公,在群里活泼得像变了个人。
最终那句话像根针,精准地扎进我眼球里。我盯着屏幕,感觉浑身血液都往头顶涌,然后敏捷冷却下来,冷得我牙齿打颤。
钥匙滚动门锁的声响响起时,我现已把手机放回原处,姿态都没变一下。他开门进来,带着一身湿气和淡淡的酒味。
他看了我一眼,大约觉得我口气有点怪,但也没多问,径自走向澡堂。水声响起,雾气从门缝里渗出来。我盯着那团白雾,心里某个当地正在渐渐结冰。
这不是我榜首次置疑。半年前他衬衫上的香水味,上个月信用卡账单上那家生疏酒店的消费记载,还有越来越频频的“加班”和“应付”。我仅仅不愿意信任,或者说,不愿意面临。
澡堂水声停了。他擦着头发走出来,只围了条浴巾,水珠从锁骨滑到胸口,沿着腹肌的线条往下淌。不得不供认,三十七岁的他仍然坚持得很好,身段乃至比咱们刚成婚时还要健壮。
他从前会成心这样在我面前晃,带着点夸耀和撩拨。现在他仅仅机械地擦干身体,穿上睡衣,然后拿起手机。
杭州。群里提到过杭州,说那里有个“安全又影响”的私家会所。我的指甲掐进掌心,痛苦让我坚持清醒。
我渐渐从沙发上站起来,羊毛毯滑落到地上。我走到他面前,伸手悄悄搭在他膀子上,能够感觉到他肌肉瞬间的紧绷。
“我想要个孩子。”我说,直视着他的眼睛,“这个月我排卵期正好是你出差前后,所以……”
他愣住了,明显没料到我会忽然提这个。咱们成婚第三年讨论过要孩子,后来由于他作业上升期,一拖再拖,渐渐地就不再提了。
他缄默沉静着,目光在我脸上迟疑,像是在判别我是细心的仍是又在闹情绪。这目光让我厌恶——他评价那些“妹妹”时是否也用这种目光?
我踮起脚,吻了吻他的下巴。他身体僵了僵,然后手臂环住我的腰——几乎是习惯性的反响。我知道他会上钩,不是由于我多有魅力,而是由于内疚。越轨的男人最简单因内疚而退让。
他垂头吻我,手掌滑进我的睡衣。我闭上眼睛,脑海里却浮现出那些谈天记载,那些显露的词语,那些同享的相片。
但我没推开他。相反,我把他搂得更紧,在他耳边轻声说:“那说好了,这周和下周,我想要的时分你都得合作。就当是……备孕方案。”
完往后,他很快睡去,呼吸平稳。我侧躺着,在黑私自睁着眼睛。雨水还在击打窗户,像很多细微的挂钟在走动。
我的指尖在床布上悄悄划着,划出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方案。他认为我仅仅想要孩子,认为这是女性到了必定年纪都会有的焦虑。
第二天早晨,阳光扎眼得不像话,似乎昨夜那场雨仅仅我的错觉。陈浩——我老公的姓名——现已穿戴整齐,正对着镜子打领带。我从床上坐起来,被子滑到腰间。
我赤脚走到他面前,伸手帮他调整领带结。这一个动作太密切了,密切得咱们都愣了一下——上一次我这样为他打领带,大约是三年前。
“不是孩子。”我打断他,手指停在领带结上,“是你容许我的,这两周我需求的时分,你都得合作。”
他笑了,那种带着宠溺和一丝不耐烦的笑:“行行行,容许你。但你得了解我作业忙——”
“夫妻协议。”我走到梳妆台前,从抽屉里拿出昨夜趁他睡着后草草写下的东西——两张A4纸,上面是我手写的条款。
“榜首,为确保备孕方案顺顺利利地进行,自协议签署日起两周内,乙方(陈浩)需无条件合作甲方(周雅)的生理需求,包含但不限于……”他念到这儿停住了,昂首看我,表情杂乱,“小雅,你这是闹哪出?”
“我没闹。”我平静地说,“你不是总说我不行自动吗?我现在自动了,你又不愿意了?”
他持续往下看,脸色越来越乖僻。我在协议里详细列出了各种要求,从时刻、地点到详细方法,写得清清楚楚,几乎像份商业合同。最终还有一行加粗的字:“协议期内,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回绝甲方合理需求,不然视为违约。”
他盯着我看了好久,最终竟然笑了,那种男人感觉自己把握了形势的笑。“行啊,签就签。不过你得容许我,这两周往后,咱们好好谈谈孩子的事,不能再这么固执了。”
他爽快地签了字,还按了手印。那一刻,我清楚地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放松——他必定觉得,这仅仅女性闹情绪的又一种方法,签了这份荒诞的协议哄哄我就行了。
他愣在那里,明显没料到这个答复。过了几秒,他轻笑一声,摇了摇头,拿起公文包走了。门关上的瞬间,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——面无表情,眼睛里却有啥东西在焚烧。
那天上班我彻底不在状况。好在我是做规划的,大部分时刻对着电脑,不需求和人过多沟通。午休时,我躲在公司天台上,给闺蜜林薇发音讯。
“薇薇,”我打断她,“我妈当年发现我爸越轨,什么都没要就离了婚,成果呢?她一个人带大我,吃了多少苦?我不能重蹈覆辙。”
林薇又缄默沉静了,这次更长。最终她说:“不论你想做什么,我都支撑你。但你要容许我,别伤着自己。”
“不会的。”我说,心里却在想,我现已伤了,从看到那些谈天记载的那一刻起,心口就破了个洞,凉风呼呼地往里灌。
下班回家时,陈浩现已在了,这在最近几个月很少见。餐桌上摆着外卖盒子,是他知道我喜爱的那家泰国菜。
“回来啦?”他走过来,很自然地接过我的包,“今日特意早点下班,陪你吃饭。”
我看着他周到的姿态,胃里一阵翻腾。这是内疚的体现,仍是协议开端起效的扮演?
吃饭时他一直在说话,说作业上的事,说周末的组织,说今后的日子。我安静地听着,偶然点点头。他越说越起劲,乃至提到了孩子——说如果是女孩,眼睛必定要像我。
我盯着那块虾,忽然没了胃口。“陈浩,”我说,放下筷子,“你还记得咱们成婚那天吗?”
“那天你喝多了,抱着我说,这辈子只会有我一个人。”我抬起眼看他,“你还记得吗?”
“小雅,”他总算开口,声响有点干涩,“我最近是有点疏忽你,但我对天发誓,我心里只要你一个。”
我在澡堂里待了好久,让热水冲刷身体,直到皮肤发红。镜子上蒙着一层雾气,我伸手擦出一片明晰,看着里边那个生疏的自己。
眼睛下面有黑眼圈,嘴角不自觉地向下撇,整个人看上去疲乏又衰老。我才三十一岁,怎样就像个怨妇了?
我擦干身体,穿上那件他从前说过很性感的黑色真丝睡裙——现已一年多没穿过了。然后我走进卧室,他正在看手机,见我进来,眼睛亮了一下。
他放下手机,走过来搂住我。我闻到淡淡的须后水香味,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、不属于我的香水味。

我推开他一点,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条领带——他最喜爱的那条,深蓝色带暗纹。
他笑了,举起双手。我用领带绑住他的手腕,打了个不算紧的结。整一个完好的进程他很合作,乃至有点享用的姿态,大约觉得这仅仅夫妻间的新情味。
绑好后,我退后一步,看着他。他被绑着手站在房间中心,目光里带着等待和一点疑问。
我走到他面前,踮起脚,在他耳边轻声说:“知道吗,我今日查了你信用卡账单。”
“那家酒店,叫‘云水间’是吧?”我持续说,声响轻得像茸毛,“在杭州灵隐寺邻近,环境的确不错。”
我铺开他,走到床边坐下,看着他被绑着站在那里的姿态。灯火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暗影,我榜首次在他眼中看到了真实的惊惧。
他犹疑了一下,仍是走了过来。我伸手解开领带,动作缓慢而细心。他的手腕上现已有了浅浅的红痕。
...